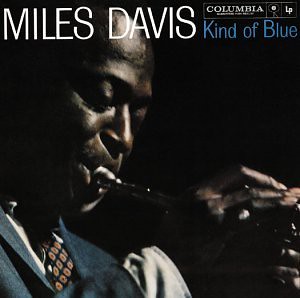餐牌上寫得輕描淡寫:Traditional French Onion Soup (Soupe a l'Oignon Gratinee Tradition)。上桌時也以為不過酥皮湯一碗,伸湯匙去舀,欲把那層薄酥敲破,誰知湯匙卻給湯咬住,動彈不得⋯⋯
/邪惡洋蔥湯
認識了F君五年,聽這餐廳的名號也就聽了五年--Au Pied de Cochon。Pied是牲口的蹄子,Cochon是豬,豬手餐廳的招牌菜當然就是豬手。館子開在彭比度美術中心附近,價錢並不便宜,我也不特別嗜吃豬手,不過五年了,反覆聽F繪影繪聲地形容這頓多年前遊巴黎吃過的豬手餐,心目中這館子已是一座巴黎鐵塔,非遊不可。站在一隻笑著喝紅酒的霓虹豬招裨下,我咬一咬牙,好吧,下個月捱麭包就捱麭包吧。
餐牌攤開來足有小報版面大,英法對照名堂排得密不透風。我問大眼睛侍應我是來吃豬的該點什麼?他眨眨眼噢當然是先來個傳統法式洋蔥湯,一杯紅酒,然後以招牌燒豬手壓陣了。就這樣,十分鐘後,那碗邪惡的洋蔥湯就端到眼前。
湯匙舀不進湯裡去。我用力破開酥皮,呀原來焦烘的薄酥下托底是一吋厚的芝士。淡黃色的,蓋在湯上,綿軟卻柔韌,與湯匙拉拉扯扯,像麥芽糖般越拖越長。我張口去咬一時咬不斷,狼狽不已,結果得動用叉子來截。這樣用叉子喝湯還是頭一遭。奇怪是芝士山下的湯一點不油膩,洋蔥早被熬成透明,只有幼線的脈絡依稀隱現在暗淡綠的清湯裡,搖晃著,如淺溪底的浮草。
/黏嘴豬手
這樣一碗湯喝完已經半飽。趁上菜的空檔捧住餐牌細看,封面上三個卡通廚子在巴黎街上合力捉拿逃命的豬。豬睜眼咧嘴一臉惶然,廚子們軟硬兼施,一個抓前蹄,一個拉後腿。這場景放在餐牌上太黑色了點吧?幽默不足反倒了胃口。但我菜已點了,酒也喝了,早是共犯,還是慌忙揭過,眼不見為乾淨。
正想著一豬生四蹄,我們只吃蹄子那身胖肉到哪去了?原來招牌菜除了燒豬手,還有豬拼盤:豬手拼豬耳豬鼻豬尾巴。我稱奇,由頭至踵吃清光,這活脫是廣東菜的風味。還有一道豬手釀鵝肝,味道太犯重了吧,脂肪釀脂肪,豈不是互相糟遢對方?另有燒豬肋骨,還有生蠔田螺龍蝦雞鴨鵝牛⋯⋯夠了夠了,我所有的,不過是方寸大的舌頭,貪不來,貪不來。
主角上場--Grilled Pig's Trotter with Bearnaise Sauce (Pied de Cochon Grille Sauce Bearnaise)--賣相其實有點醜:暗褐色的蹄子灑滿焦麵包屑,伴碟是一堆名副其實的french fries。我條件反射地馬上剔走對泣了半年的薯條,然後提刀剖開豬手。又嚇了一跳:刀子拖下去彷如無物,蹄肉如豆腐順勢倒地,奶白色透明軟膏裹夾粉紅色的肉,猶自在油光中抖動。我嚐了一口,表皮和軟膏入口即化,淡淡卻厚實的滋味黏滿一嘴,剩下的嫩肉也不耐嚼,牙一咬就散開,也是淡淡的,但簡單鮮美。
這一點淡,大概是法國菜的精髓。沿途吃來,由街頭的薄戟可松,咖啡座裡的糕餅甜點,到平民餐館裡的家常菜,無一不是淡淡的,和英美意式菜的濃郁鹹重大相逕庭。要堅持這點淡並不容易:原料要鮮,煮法要嫩,吃起來本身就滋味,不必以濃味遮醜;也正因為底子夠,調味就更加要淡,否則喧賓奪主,白白浪費了原味。
侍應走過,向我打手勢:用手吃,用手吃。又指指桌上一盤檸檬水。我於是放下屠刀,人手執豬手,果然吃得稱心,只是這樣滿手油的吞吐骨頭,和四周的高貴格格不入,一邊滋味,一邊尷尬。想起紅樓夢裡,曹雪芹把薛寶釵的兄嫂夏金桂寫成嗜啃骨頭的妒婦,每天都得殺雞烹鴨,將肉賞給下人,然後油炸焦骨頭自己慢慢啃著下酒,以側寫她的殘暴霸道。啃骨頭從來不優雅,難怪鄰座的女士們點的都是海鮮,切一小塊白肉,放進櫻桃小口,再啖一口白酒,抿抿唇,口紅猶在,把我這邊廂的血肉戰場輕易比下去了。對女生來說,口腹之慾向來與美麗互斥,必須痛捨其一。
/冰裡來火裡去
未幹完那一盤半爪,已經吃撐了,很想學晴雯喊一句:我再也不能了!然後趁微醺倒地酣睡。但F曾千叮萬囑一定得吃甜品。鄰座的太太向我推介火焰薄戟(crepes Flambees)。我本是薄戟迷,但肚皮和舌頭再受不了,只能來點清淡的。於是點了青蘋果雪葩(Sorbet Pommes Vertes)。雪葩比較瘦嘛,我阿Q。
說是雪葩,也一點不簡單。雪球細滑,甜;嵌滿青蘋果肉,酸;灑上肉桂粉,微澀;浸在蘭姆酒裡,火辣。我垂下頭什麼也不想了,一羹一羹舀下去,吃一口眯一下眼睛。直至玻璃杯底剩下混白了的一點蘭姆酒,淺淺一圈,為這場盛宴劃上完美的句號。
/Baguette, Coffee & Cigarette
然而我想,生活的味道並不在豬手雪葩洋蔥湯,而是當味蕾歷盡種種高潮後,喝粗茶吃淡飯依然不減滋味。色慾無窮,身體是永遠填不滿的,過日子的道理反而在法包的空純,齋咖的濃苦,和煙草的乾澀--粗糙基本卻耐久,這才是日常的滋味。所以占渣木殊的《Coffee & Cigarette》裡,讓角色細細舖展喜怒哀樂的,是咖啡桌,而不是餐桌;所以逛書店見法文小說都是素淨的封面--這些都是維生的食糧,有形的無形的,如水和空氣。花火放完了,更覺呼吸清新空氣的奇妙,更覺白開水的甘甜。
走出餐廳,我抬頭瞄一瞄那隻還在喝酒的霓虹豬,腦裡哼著向陳綺貞借來的《靜靜的生活》:豬手以後,靜靜生活;雪葩以後,靜靜生活⋯⋯
Au Pied de Cochon
6 rue Coquilliere - 75001 Paris
www.pieddecochon.com
080605 (待續)